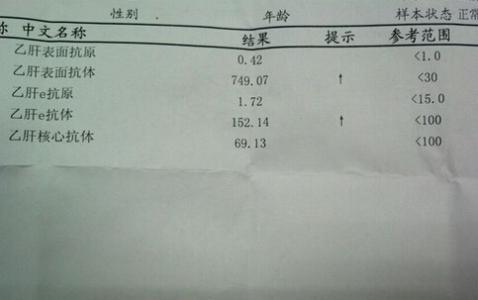【版權聲明】本文由《晚點LatePost》授權騰訊新聞獨家發布,未經騰訊公司許可,不得轉載。
文 |《財經》記者 紀麓
編輯 |宋瑋
無數次歷史經驗證明,對抗疫情最好的辦法就是科學和真相。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在武漢引起疫情後不久,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帶領團隊開始研究家庭群組的聚集感染。研究發現在家庭內密切接觸的情況下病毒攻擊率很高。該報告於1月24日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在國際上首次提供確鑿證據,說明此病毒不僅能夠人傳人,而且在此階段其人傳人的能力非常強。
當時港大的研究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出現家庭內聚集感染的風險很高,整個家庭中有83%的成員受到感染。
可就在1月28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規定,規定稱:如當地發生強度較大流行,醫療資源緊張時,輕症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可采取居家治療和觀察。
此後武漢多個病患案例證明,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的家庭成員也相繼發病。而各地因家庭聚集而集中確診的病例更層出不窮。2月21日,國家衛健委發布第五版防控方案,新版方案修正為:無症狀感染者應當集中隔離14天。
研究團隊當時還找到一名無明顯症狀但肺CT有輕度異常而痰液中檢出病毒核酸的感染者,首次敲響無症感染傳播病毒的警鍾。為國家果斷應對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武漢“封城”至今近一個月,暴露出中國醫療體系以及傳染病防治的某些短板。這體現在公布疫情的及時性、醫療資源的調配上,也體現在研究領域的多個方面:
包括高水準臨床研究的稀缺;高水準流行病學研究的缺位;診斷試劑與藥物研究技術儲備不足;醫療救治、疫控及病毒學研究是擰成一股繩、共同作戰,還是各自忙碌,缺乏溝通?
病毒學家金冬雁對此深有體會。他從2003年以來堅持對冠狀病毒的研究。他回憶17年前SARS疫情暴發後,“中國可能有成千上萬個科學家在研究冠狀病毒”,但SARS消失後“研究也停止了,跟風趕潮流的多而堅持下來的極少,充分顯示一些中國學者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他說。
金冬雁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也是中國自己培養的分子病毒學家。1982年他考入中山大學生物化學專業;其後他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攻讀醫學博士,並留在病毒學研究所工作;之後前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1999年回到中國,在香港大學任教至今。
他多年來致力於腫瘤病毒分子生物學及病毒與細胞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相關領域內國際公認的學術帶頭人之一。2020年他剛剛當選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
金冬雁說,在英美醫療體系裡,微生物學科和病理學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我國醫院內的微生物學、傳染病學及病理學專家則未能對其他各科以至整個醫院發揮指導作用。
此次疫情中,呼籲了很久才開始進行的屍檢工作,便是上述忽視病理學問題的直接體現。
病毒是可怕的。人類本不該一次次重蹈覆轍。
以下是《財經》雜誌對金冬雁教授的專訪:
“康復者馬上再感染,是違背病毒學和免疫學基本原理的。”
《財經》:最近有新聞稱病愈出院者二次患病,檢測結果是雙陽。有人推測是SARS-CoV-2病毒發生了某些變異,作為病毒學研究專家,你的看法是?
金冬雁:康復者馬上再感染,這是完全違背病毒學和免疫學基本原理的。人體對抗病毒靠免疫反應,免疫反應產生後再遇到病毒會被激發,不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消退。至少6個月、一年內不會再受感染。
SARS-CoV-2病毒的變異率明顯低於SARS-CoV,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它會迅速變異導致出現免疫逃逸。鍾南山院士團隊2006年的研究表明,SARS康復病人體內至少兩年內仍可檢測到具有保護作用的IgG中和抗體。可以推斷SARS-CoV的情況應與此類似。(注:IgG抗體是保護性中和抗體,代表你感染過相應抗原。)
治愈者或高或低都有抗體,再次遇到同樣或者十分相似的抗原時,抗體免疫系統受到激發,還會大量產生抗體。採用治愈者的抗體救治重症患者,是可行的辦法之一。如果說治愈者還能馬上再受感染,近乎不可思議。真如此那也不必再研究疫苗。
我們從事疫苗研究的人常說,最好的疫苗就是不發病或症狀極為輕微的感染。如果實際感染過都沒有保護作用,那疫苗也不會有用。
《財經》:國家衛健委新冠病毒診療方案提出“血清療法”,就是用已治愈者血清裡的抗體來治療重症患者。
金冬雁:用病人的恢復期血清來治療重症的病人,這是屢試不爽的,值得一試。
人體感染病毒後,後期病毒會被人體產生的抗體所清除,抗體療法也是這個原理,不同的只是借用別人身體所產生的抗體,所以又稱為被動免疫。與此相對,接種疫苗後產生抗體中和病毒,則是主動免疫。被動與主動免疫,都可以達到抑製和清除病毒的目標。
但“血清療法”也是有副作用的,血清裡面可能有未知的病原,也可能有致敏原可引起過敏反應。用別人的抗體性質跟輸血類似,就是應急,隻適用於危重病人。
《財經》:四川省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雷學忠曾表示,病愈後再確診的病例“更大可能是少數病毒的持續殘留”。學術上是否存在“病毒殘留”這種說法?
金冬雁:病毒持續殘留不是科學語言。如果是持續性感染,除非病人是免疫缺損,否則可能性極低。
理論上病人無症後可能通過糞便或腸道經常排病毒一段時間,過去也有一些報導。但這種情況很少,現在也不是這種情況,不應以獵奇的心理去放大。
《財經》:你認為病人“二次複發”最可能的原因是什麽?
金冬雁:最可能就是出院時沒測準,承認這一點是最直接了當。
病愈時核酸檢測可能是假陰性,或者病毒載量降低後由於試劑靈敏度及取樣等關係沒檢出。如果要排除沒測準的概率,應同時測抗體,比如,抗體有四倍以上增高才是進入恢復期。最好的辦法是量產抗體試劑作輔助診斷,用其他奇奇怪怪的理由去解釋,根本違背常理。
《財經》:新冠肺炎治愈者是否存在後遺症?
金冬雁:目前看不會比SARS更嚴重。SARS的後遺症實際很多是激素治療後遺症,而不是SARS本身的後遺症。以SARS為例,絕大多數患者都可完全康復,只是重症患者完全康復的時間更長一些。
《財經》:我們現在掌握的信息,有治愈患者肺部纖維化仍存在。
金冬雁:肺部纖維化確實不可逆轉,也無藥可治。
但過往研究表明,SARS-CoV感染所產生的肺局部纖維化還是可以被吸收被清除,最後完全自愈,只是需要一定的時間。重症及年長患者恢復更慢,但大部分人都是能夠百分百完全恢復的。
《財經》:為什麽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會呈現前期症狀不明顯、潛伏期長、傳染性強而致死率相對較低的特性?
金冬雁:病毒跟宿主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拮抗的關係,我比喻它為“拔河”。這個過程中,病毒和宿主彼此要適應——病毒適應人,或者人適應病毒。
病毒傳染性變強,致病性就轉弱——這就是病毒逐漸適應人體的過程,是病毒進化的自然規律,並不意味著它有多特別,有多狡猾。
相反,傳染性弱的病毒,致病性比較強。此病毒感染前期症狀不明顯,甚至出現無症感染者,確實為防疫帶來很大挑戰。但目前來看,新冠病毒感染的潛伏期與SARS-CoV和MERS-CoV類似,一般不超過一星期。尚並無證據表明其潛伏期特別長。
《財經》:很多人在討論病毒的變異性,它在短期內是否有變異出另外一種形態的可能性?
金冬雁:肯定有變異。但它的突變率和SARS-CoV比,相對較低。
SARS-CoV的源頭是蝙蝠,蝙蝠非常適應這種病毒,但這種病毒可能不太適應高等哺乳類。MERS-CoV的中間宿主是駱駝,駱駝有發病但不嚴重,說明該病毒已經比較適應駱駝。但它感染人體引起的症狀就非常嚴重,推斷它在人類中仍未充分適應。
那麽SARS-CoV-2是不是也經過了一個中間宿主,可能已經比較適應這個中間宿主,而這個未知的中間宿主也可能與人類比較接近。所以SARS-CoV-2的突變率較低?這是一種推測。
《財經》:這是否意味著它不會變成更致命的一種病毒?
金冬雁:從進化角度來說,進化是要對病毒自身有利。它變成更強的病毒,並不對自身有利,因為它把宿主殺光了,自己也無處藏身無法繁衍。變異成特別凶惡、毒力很高的病毒,這是意外,不符合一般規律,可能性很低。
從研究結果來看,從香港患者身上檢測出來的毒株和武漢患者身上的毒株差6個核苷酸,這說明變化很少。整個SARS-CoV-2病毒有3萬核苷酸,6個隻佔極小的比例。(注:核苷酸是病毒的遺傳物質,控制病毒的複製和決定病毒特性。)
“不是說病毒消失了我們就勝利了,它不消失我們就失敗了。”
《財經》:疫情的轉捩點可能何時到來?到來的標誌是什麽?
金冬雁:最主要是先掌握實情,疫區的真實情況如何,到底“敵人”有多強大。什麽時候到頂,這個我預測不了,不能拍胸脯說,哪天可能到高峰到轉捩點。
如果還有很多人現在都沒有診斷出來,有很多無症狀感染者,他自己不覺得得病,喉嚨痛了一下就過了,可能已經傳染給別人了,這是十分危險的。現在的實際情況非常不明,不查清楚怎麽設定防控策略?
未來只有兩種情況,一是病毒在人類完全消失了,像SARS-CoV一樣,雖然致病性不低,但沒有在人體裡落地生根;另一種情況,就是病毒完全適應了人類,傳染性高但致病性低,成為另一種社區獲得性人類冠狀病毒。
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依靠疫苗同樣可以將SARS-CoV-2病毒在人體內完全消滅,就像我們利用疫苗消滅天花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一樣。
《財經》:病毒完全消失和完全適應人類,哪一種可能性更大?
金冬雁:實際上會消失或者不會消失,都沒什麽了不起。不是說它消失了我們就勝利了,它不消失我們就失敗了。
這兩種情況我們都要做好充分準備,各有相應策略去應對。只要應對得當,人類在任何一種情況下仍然可以取得最後的完全的勝利。
《財經》:如果後一種情況發生,人類將面對什麽?
金冬雁:那就要在病毒變弱之前,竭盡全力把盡可能多的危重患者從鬼門關救回來。現在大概有10%-20%的人出現重症,需要使用ICU,致死率是2%、1%或更小,武漢大概是3%。
我們要把危重病人及早識別出來,把這些人命救回來,這是現在臨床最大的任務,人命關天。
《財經》:目前疫情已經在全球蔓延,包括在氣候炎熱的國家。之前人們期盼它像SARS疫情一樣隨著氣象變熱而消失,是否不可能發生了?
金冬雁:SARS-CoV是由於防控隔離等措施慢慢發揮作用,而且病毒在人類傳代後傳播力也有所減弱,所以在氣象變熱之前疫情退卻。
從動物跨越種間屏障傳播到人的病毒,常常會由於未知的原因,自然而然地消失。至於消失的原因,溫度未必是關鍵。新加坡氣溫一直較高,但SARS-CoV-2仍有一定傳播。
SARS-CoV-2在人類傳到第三四代或更多代,傳播力到底是不是減弱,致病性有沒有變化,都十分值得關注,應花大氣力盡早摸清情況。如果病毒傳播力確實減弱而各方面防控措施也發揮作用,疫情仍可能無疾而終。歷史上類似情況也出現過多次,例如艾滋病毒從靈長類跳到人,十幾次中只有三四次成功。
今天病毒在武漢爆發,現在已經有5、6萬人感染。人們開始都笑話管軼教授說10倍起跳,我認為他有他的道理。回過頭看,起碼他這個預見是對的,真是10倍起跳。
如果感染人數到了一定程度,只能等待群體免疫,等到30%、40%以至更多人都有抗體的情況下,就會有傳播阻力,阻力越來越大,最後傳不起來,自然就阻斷了。如果這一次在第一年守不住,將來就得靠疫苗了。
“不把基本情況摸清,搞什麽策略都是無本之木。”
《財經》:此次疫情是否會在全球大規模爆發?
金冬雁:病毒在很多國家及地區的傳播仍是早期,不好說。
《財經》:目前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待新冠的策略很不一樣,國內是強製隔離,日本則不主張隔離,新加坡的防控也相對寬鬆。
金冬雁:不同的決策殊途同歸。中國香港是盡量堵截,堵截不了就盡量拖慢病毒的蔓延速度。新加坡說,如果傳播到一定程度我們就棄守,不再追蹤密切接觸者,專注救治危重病人。所有病毒性疾病的爆發都有規律可循,有一些是很難擋住的。
香港一開始做得很好。但後面由於決策不果斷,錯失了最好的防控機會,現在有了社區感染的苗頭。只希望戒慎恐懼,步步為營,防止社區大爆發。
《財經》:鑽石公主號選擇全員在船上隔離,結果從1人致全船621人感染,這是否是個錯誤的決策?
金冬雁:事後看船上隔離效果確實不好,但問題出在哪還是要先查清。是不是你把船上的人放到岸上隔離就好呢?不好說。如果隔離方法不對,無論船上還是岸上,效果都不會好。
《財經》:如何看待鑽石公主號上高達17%的感染率?
金冬雁:過去香港淘大花園發生過SARS-CoV的超級傳播事件。源頭的腎透析病人可能因為免疫抑製而釋放大量病毒,然後可能通過汙水管道形成氣溶膠傳播。
鑽石公主號應該也有超級傳播者,至於受病毒汙染的是通風、排汙、食品還是其他什麽東西,是不是氣溶膠傳播,都有待查明。你把人關在那兒,說是隔離,但一直還是每天50例、60例、100例新增,實際上這種隔離沒起到作用。
同樣來看武漢,我們雖然把武漢封了,但並沒有完全堵截住病毒。那麽病毒到底通過什麽方式傳播?是家庭內傳播、醫院內傳播、還是社區內甚至樓上樓下傳播,還是通過糞渠、垃圾、通風系統?你不把這個情況摸清,兩眼一抓瞎,是非常危險的。
現在據報導已經有抗原抗體檢測試劑,應該盡快把這個量產,真正實現一滴血很快就可以查出患者的抗原抗體。有IgG抗體的可能是過去受過感染,有抗原的或者有IgM抗體的則是正在受感染。(注:IgM抗體是靈長類動物感染後最先出現的抗體。)
現在做核酸檢測技術難度大,我們應該趕緊通過抗原抗體檢測把基本情況摸清,否則搞什麽策略都是無本之木。
《財經》:給所有確診和疑似患者都做抗原抗體檢測,工作量太大。
金冬雁:我們要解剖麻雀,可以從幾個代表性居民小區或部門做起。應該組織力量把這個基本疫情摸清楚,實事求是,再來設計甚至改變防控的策略。
檢測對象不僅包括確診和疑似病人,還應包括小區或部門中的所有健康人。通過檢測查清有多少人受過感染已恢復,多少人正受感染,以及多少人無症或輕症帶病毒。
我們的防控策略需要因應實際情況來設定及修改。例如在受感染比例較高的情況下,就不能再大量集中隔離密切接觸者,因為在感染者已經很多的情況下,集中隔離密切接觸者就不再有意義。他佔著床位,真正中症或者重症的病人就無法收治。
《財經》:為什麽湖北地區的病死率遠高於其他地區?
金冬雁:目前看到的數據裡,湖北以外的死亡率大概0.6%。流感是1%,從絕對數字來講,流感死的人也不少。湖北省外的情況是比較接近真實的,因為醫療資源豐富,很多地方拚命把患者都找出來了。就是說如果功夫做到家,是可以降低病死率的。
武漢為什麽致死率更高,第一有可能是重症的治療不及時不恰當,包括有些可能是激素造成的繼發感染致死;第二,實際上武漢計算病死率的分母可能要大得多,因為有很多人可能沒診斷出來,他無症或者非常輕症,根本沒就醫。很多可能已經自愈,只能通過檢測抗體才能查出來。
正因為如此,現在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趕緊摸清實際情況,確定後才能按照實情重新判斷。
《財經》:你如何看待武漢封城,假如早半個月、早十天封城,會如何?
金冬雁:封的時候公共醫療體系已經超負荷了,一開始還是流感高峰,很多人是得了流感跑去醫院,結果被少數的SARS-CoV-2病毒感染者傳染。
封城肯定是有用的。但是作用在哪?這個作用是把病毒消滅了,還是只是把病毒傳播拖慢?更多專家覺得是拖慢了。
封城成功的地方在於阻止病毒從武漢和湖北流出。我們封城,阻止人員流動,效果如何?有多少人實際上是無症感染?有多少人是輕症感染?有多少人實際上在感染但沒有就醫?現在是很多問題都沒搞清楚。
封城後病毒還在傳播,到底是怎麽傳,主管部門要動起來,組織疾控及其他力量,花大力氣解剖麻雀,把原因給搞清楚,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武漢。
“真正高水準的臨床研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們現在最缺的。”
《財經》:你經歷過SARS疫情,相比之下,這次疫情防控上有何進步?還有什麽不足?
金冬雁:有很多進步的地方,比如很快就把病毒分離出來,測定序列,和全世界分享等等。
不足之處,也是最最重要的,是基礎跟臨床,臨床跟疾控,整個配合不夠。CDC(中國疾控中心)、衛健委和地方政府的職權不夠分明。CDC上面有疾控局,疾控局上面有衛健委,裡面的關係沒有理清。從疫情爆發到1月20日,決策出了一些問題,造成了兩到三周的耽誤,這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將來一定要好好總結。
《財經》:根據你的觀察,此次疫情給醫療體系和傳染病防治體系帶來哪些啟示?
金冬雁:這應該等到疫情結束,或者是告一段落時認真總結,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目前來看,方方面面各自為政,配合較差。醫院由醫政醫管局主管,跟疾控及病毒學研究沒有擰成一股繩。基礎做基礎,臨床做臨床,疾控做疾控,大家各不往來。
從研究的角度來講,香港大學在深圳醫院做了家庭群組研究,1月24日就提出在家庭密切接觸下病毒的攻擊率很高。研究團隊還找到了一位自述無明顯症狀但肺CT有輕度異常,最後查出SARS-CoV-2病毒核酸的年輕感染者,第一次敲響無症傳播的警鍾。這項研究為國家制定和修改防疫政策和舉措提供了有力的科學根據。
真正高水準的臨床研究至關重要,能發揮很大作用,我們現在缺的就是這些。(注:家庭群組研究指通過對家庭成員中某種疾病的發病情況進行調查分析,來顯示某種疾病在家族中的傳播特點。)
《財經》: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疾控中心、衛健委和政府部門,分別應承何責任?
金冬雁:疾控中心主要起技術指導的作用,疫情公布是在衛健委。我們1月18日之前就知道部分情況,但並未看到對疫情的及時公布。
這一次暴露了我們醫療體系及傳染病防治體系的一些瓶頸和短板。在英美體系裡,微生物學科和病理學科的作用非常重要。但現在我們的醫學微生物學、傳染病學和病理學專家基本上不能對全院起指導作用。包括呼籲了很久才開始做的屍檢,說明病理學科的重要性被忽視。
《財經》:關於臨床用藥,你觀察到的現狀是什麽?
金冬雁:規範治療,不能亂治。過去SARS用激素治療,這一點我歷來非常反對,用激素治病毒病完全是飲鴆止渴,後患無窮。
SARS、MERS或者現在NCP,用激素後看起來立竿見影,炎症減少,或者說是細胞因子風暴受到抑製。可治標不治本,病毒會飆上來,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機會也因此提高。甚至有一些人,接受激素治療後有可能變成超級傳播者,這是非常危險的。
最近武漢醫院發現有患者深部真菌感染,很可能跟激素有關。激素用了以後,真菌、衣原體等病原體接踵而來。激素必須在病毒已完全受控的大前提下,才能發揮減緩細胞因子風暴的作用,其發揮作用的窗口很窄,使用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他各種藥物,包括干擾素,其實都各有毒副作用。干擾素用於病毒感染早期可發揮抗病毒作用,但在感染後期,則往往有較嚴重副作用,對細胞因子風暴可能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即使有明確抗病毒作用的干擾素,使用時仍應謹慎。
治療方面需要大家有共識,需要醫學病毒學家、臨床病毒學家還有危重醫學、呼吸科,各方面溝通配合。不規範治療很危險,可能一些同胞的生命因此就失去了,這是非常可悲和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