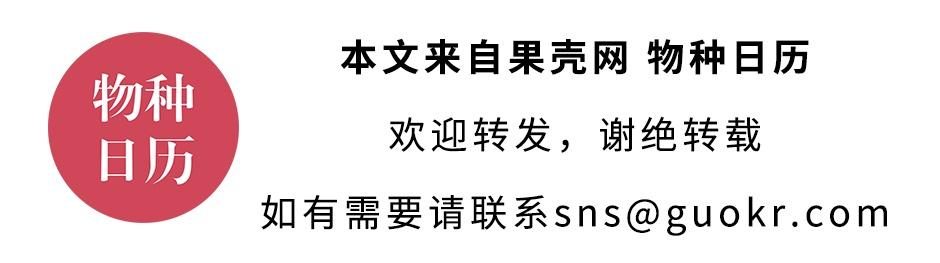兩位來自江西贛州全南縣的年輕人——劉蘇良和胡躍清,主業為養殖竹鼠,副業是工作之餘拍攝影片上傳到互聯網,分享自己的養殖經驗和生活點滴。大約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二人以ID“華農兄弟”在網上發布系列影片,隨後爆紅。

華農兄弟之所以受歡迎,按網友的說法,多半是因為他們那些千奇百怪的、“一百種吃掉竹鼠的理由”。他們發布的影片裡的場景通常很簡單,大都集中在養殖場、河邊、農家小院等幾個固定場所。較為常見的模式是,博主來到自己的養殖場,看似隨意地選擇一隻竹鼠,進行一番健康分析後,以各種理由宣布其最終命運:“這隻竹鼠中暑了,沒辦法,只能給他燉了”;“這隻竹鼠長得太胖,太能吃了,不如拿去紅燒”;“這隻竹鼠圓嘟嘟的,十分可愛,一定很好吃,我們去河邊烤了”。隨後鏡頭一切,幾秒鐘前還活蹦亂跳、憨態可掬的竹鼠已被屠宰去毛,或是直接被砍作一坨血肉模糊的肉塊,被靜靜地置於碗中,加以佐料,等待烹飪。這一系列形式相似、內容又各不相同的影片引發了火爆的圍觀效應,華農兄弟人氣亦急劇攀升。截止2019年1月,兄弟二人的抖音账號已有180萬粉絲,微博粉絲130萬,Bilibili平台粉絲數已超過244萬,總播放數達到1.9億。
無疑,華農兄弟稍顯笨拙的口才、竹鼠可愛的外形,以及“上一秒好萌,下一秒去世”所營造出強烈的敘事和視覺衝突,都是影片的“趣味”所在。然而不得不說的是,在發笑之餘,這些影片同樣引發了某種十分恐怖的感受。在那個小小的養殖場裡,在那個由幾百個水泥格子區隔的世界中,身為一隻竹鼠,無論你是健壯或是孱弱,漂亮還是醜陋,都隨時隨地可能會被從天而降的巨手捕獲,被拎著尾巴來到河邊,鏡頭切換,隻留下白骨一盆。

隨機屠宰為何充滿誘惑?
事實上,除了竹鼠之外,華農兄弟的影片創作還包括了種象草、摘板栗、做糍粑、吃木槿花、與狗玩耍、拿蜈蚣泡酒等種種真實有趣的鄉村日常生活。可以說,一方面,他們通過新媒體再現了農村日常生活的生動景觀,另一方面也向觀眾打開了養殖業不為人知的內部世界,以及這一世界的支配邏輯。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一看似“反優生學”的隨機屠宰,是如何充滿了吸引人觀看的誘惑力的?又是如何通過新媒體中介和再現,最終呈現為一個令人發笑的景觀的?他們的行為本身和表征形式對於人和動物來說又意味著什麽?
一個簡單的解釋是,在華農兄弟的影片中,竹鼠從動物到食物的屠宰過程被有意剪掉了。根據他們介紹,這一過程往往長達一個多小時,而經過精心剪輯,活物和死物間的影像被縫合成為了一瞬間之事,這種反差帶來的體驗是:上一秒將竹鼠當成毛茸茸可愛的小活物和下一秒心安理得享受一盆食物之間,似乎並不存在認識上的斷裂,竹鼠經歷了某種無痛化的死亡。由此觀之,這一切可能首先是一個視覺效果的問題,在鏡頭的跳切之外,在時間的壓縮中,竹鼠的死亡被折疊了。但問題在於,同樣被折疊了的還有觀看者的感受力、對死亡的想象,以及對“竹鼠是否會在被屠宰的過程中感受到痛苦”的追問。
在一些動物權力理論學者看來,這一問題恰恰是人類以自身利益為重,對動物進行殘酷對待的“物種主義”之關鍵。誠然人類具備更多的理性和自我意識,但是人和動物在對快樂和痛苦的感知上具有同等的道德意義,人和動物感受到的痛苦相等,道德上的惡也就相等。換言之,儘管華農兄弟可以養殖竹鼠、拍攝影片,但在對一把利刃的感知上,一個人和一隻竹鼠並無區別。因此,無論這一刀下去砍在誰的身上,所承擔的道德重負幾乎是一樣的。因此給予動物“平等的考慮”(equal consideration)便十分重要——這不意味著必須要讓竹鼠定期體檢、上瑜伽課、住在24小時恆溫的辦公大樓裡,而是意味著,人類可能需要在觀念和行動上,對不同物種在相同數量的苦樂利益上付出相同程度的考量。

竹鼠雖可愛,緣何難共情?
如果說互聯網短影片這一再現形式有效地遮蔽了竹鼠的死亡過程,並由此消解了死亡過程所可能包孕的道德負擔及相關感受的話,對中國人來說,“竹鼠那麽可愛,為什麽要吃它”其實從來不是個問題。只要稍加考察便會發現,竹鼠在中國傳統中被劃分到“可食用”的類別已頗具歷史。一旦從這個視角出發,《本草綱目》中的記載幾乎就是一個大眾點評式的描述了:“竹鼠食竹根之鼠,形大如兔,肉味甘補中益氣解毒。”文人亦對這一物種有所吟詠,蘇軾《竹?》一詩中寫道,“野人獻竹?,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費罝網,”彼時竹鼠之繁,可見一斑;而蘇轍則在《次韻子瞻竹鼠》中則借鼠比興,感時傷懷:“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癡與瘦黠,稟受不相仿……一朝受羈絏,冠帶相賓饗,愚死智亦擒,臨食抵吾掌。”
這種“臨食抵吾掌”的愚物,為什麽不能喚起觀看者的類似於蘇轍的同情呢?為什麽在華農兄弟眾多的追隨者那裡,認可竹鼠的美麗和認可同一隻竹鼠的美味是一件毫無障礙的事情?我們大可將這一切歸結為數位時代的後果之一:某種扁平化的景觀,某種比現實更為真實的“擬真”,或是在無數個碎片化的後現代時間之中情感的消逝。歸根結底,竹鼠的“原罪”在於,作為一種動物,它對人類而言,終究並非是哈拉維意義上的“伴侶動物”;竹鼠不像狗一樣,是和人類共同進化、同時深刻地形塑著人類主體同一性的物種。因此對於竹鼠(之死)的觀看,事實上非旦不會引發共情,反而恰好更為深刻地間隔了人和竹鼠、人和食物、人和非人之間的邊界,確認了人和竹鼠非共生性的物種關係。

從這一意義出發,即使華農兄弟不刻意剪掉那些屠宰場景,影片恐怕也不會遭到冷遇,或許會更受歡迎。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說動物解放理論家從邊沁的思想理路出發,倡導以感覺能力為標準,試圖去重估繼而去承認動物的主體價值,那麽在人們對竹鼠影片的觀看中,在對人這一物種之外的他者之死的差異性的觀看中,人反而確認了自己的安全位置,讓動物分類法再次變得有效,也讓自我免於動物的逼視,尤其是動物所包含的、哲學意義上的、對主體邊界可僭約能力的逼視。這是一種頗為反諷的局面:在一個開放的互聯網空間中,在這個不時宣布人的同一性消亡、主體性消解、人的存在形態可能變得更為多元而豐富的時代中,人們卻癡迷地凝視著竹鼠,從一隻愚物的生與死中確認著自己的人類身份,同時又是以一種關閉、退守的姿態,去面向人類日益模糊的主體邊界,去“開敞”主體的“生成”(becoming)空間。
我們不能妄斷互聯網上的觀看者們是否並非無法感知到竹鼠的痛苦,同樣,我們似乎也很難用想象力的匱乏,來一勞永逸地解釋人們是如何選擇性地忽視了那些被有意遮蔽了的屠宰情景。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對華農兄弟影片中所展示的那個動物養殖世界的無知狀態本身,便是對“仍然有物種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這一事實的懼怕、拒絕與再度擁抱。
苛責那些手機螢幕之外的人們為什麽不能對贛州某個角落裡的一隻竹鼠發生共情,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畢竟不是所有的竹鼠都會被他們帶去廚房——有那麽一兩隻面容姣好、毛色出眾的白色竹鼠已然成為新晉網紅,穿上了廣告商寄來的特製衣服。無論是對於竹鼠還是對於人來說,必要的不僅僅是如何恢復對“我”之外的弱小者的命運的想象力,或許同時也是去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在死亡的支配下,動物和食物之間,“萌萌的必死之物”大概是一個更為安全和美好的答案。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胡亮宇,編輯:黃月、傅適野,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