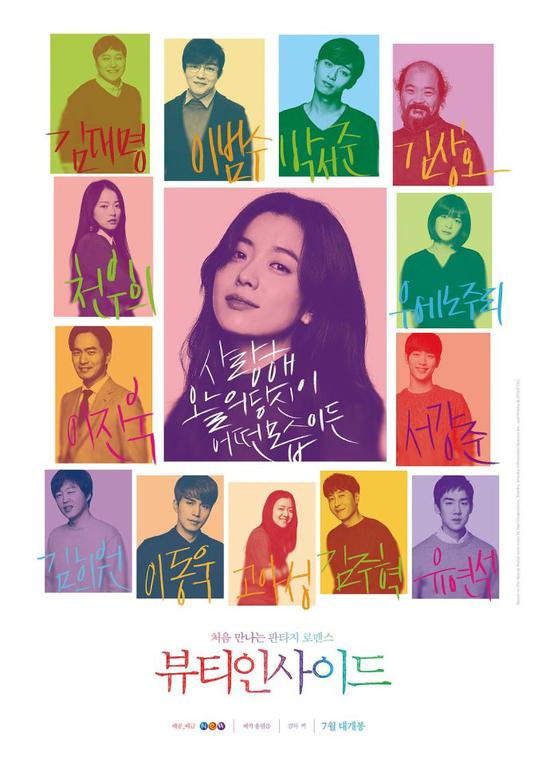原文標題:《我愛你!》:用韓延的方式解決哈內克的難題
文丨石川(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05電影網專稿 韓延新片《我愛你!》延續了導演本人關注人生困境的一貫視角,依然將注意力鎖定在先天疾患、絕症、死亡等人類無解卻又不得不去面對的終極議題上。只不過,這一次,《我愛你!》將敘事的重心,從青年群體轉移到了中老年身上。
過去十多年,青春片一度引領了中國本土類型電影的風氣之先,但很少有人像韓延那樣,在青春片的浪漫軀殼之下,展開的卻是一些不無沉重和壓抑的“疾病敘事”。他的《第一次》、《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無一不是這樣的作品。
按照常理,這並不是一個對青年觀眾有足夠吸引力的議題,但反過來,卻能折射出韓延自身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創作態度和勇氣。因此,他以一人之力,讓本土青春片的創作流向在中途拐了一個大彎,將其從浪漫虛浮的半空,拉回到有點泥濘,卻又不乏生機勃勃的滾滾紅塵當中。
一個年輕人,碰到生、老、病、死這些讓人頭痛的話題,不逃避,不推諉,敢於直視,敢於擔當,敢於“雖千萬人吾獨往矣”,這至少說明,他已經邁過了懵懂青春的門檻,達至“成熟”的人生彼岸。在本土青春片的一眾創作者當中,韓延最具這種“成熟”的品相。除了前述三部,還包括他前不久的《人生大事》,都可以被視為本土青春片創作走向成熟,回歸現實主義的標誌。今天的《我愛你!》,也正不過是韓延在現實主義創作路徑上的一次延伸和拓展。

《我愛你!》的故事發生在當代都市的尋常巷陌,其基本的敘事策略,也依然是透過對角色生活訴求和情感邏輯的挖掘、鋪排,來建構人物之間的戲劇衝突,在人生的極度殘酷又極度浪漫之間,保持著一種韓延式的敘事張力。
倪大紅飾演的空巢老人常為戒,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角色。他腰懸麒麟鞭,怒打不孝子,開著一輛破舊的“三蹦子”,穿行在都市的大街小巷,像個遊俠一樣,路見不平,便會金剛怒目,拔刀相向。他和惠英紅飾演的孤寡拾荒女李慧如一起,幾經掙扎,終於從世俗習見中破繭而出,在人生晚境中達成了自我價值的重建。這個結局樂觀、陽光、正能量,是對現實人生的一種理想化投射。
相比之下,梁家輝飾演的謝定山和葉童飾演的趙歡欣,以及那一對因早年愛情挫敗而抑鬱終生的老年情侶,他們的命運則顯得更為慘淡和不堪。在他們身上,纏繞著太多讓他們無法掙脫的世俗枷鎖。除了年老體弱、罹患絕症這類自然因素之外,來自社會、子女以及傳統倫理習俗的壓迫,也讓他們對自己生命的最後旅程感到無生趣。

劇情似乎因此呈現出冷、暖兩種色調的對衝:一面是撕開現實的偽裝,將其殘酷、陰冷的一面展現出來,一面又以常為戒和李慧如的掙扎、跳脫,最終遠離都市,歸隱田園的浪漫結局,來為複雜難纏的現實困境,提供一種包裹著溫暖色系的想象性解決。影片也因此而顯得既現實又浪漫,是一種20世紀中國文論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合體。
然而,同樣是關於愛、衰老、病痛、死亡的故事,哈內克的《愛》讓人看到卻是另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哈內克的影片,採用的是一種嚴峻得近乎冷酷的寫實主義,因而《愛》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個令人絕望和窒息的場景。如同一個正在不斷下沉的溺水者,越是掙扎越是無力。《我愛你!》中的謝定山和趙歡欣,原本也可以選擇哈內克的方式,讓整部影片成為一個沉重而悲愴的黑色故事,但韓延沒有那樣做。
韓延對一個原本暗淡無光的故事,採用了一種“提亮”處理,讓觀眾在溺水的窒息中,還有一絲可以浮出水面,大口呼吸的機會。他在劇情中插入了一個“高光時刻”,讓四位老人彼此滋水嬉戲,讓天空中浮現出若隱若現的彩虹。這樣一個老年童話般的場景,多少可以讓觀眾暫時忘卻命運的不公,讓堅硬和粗糲的現實,得到些許的升溫和軟化。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觀眾是比較偏愛這樣的柔性的處理方式的。因為儒家講究中庸,不論是是為人處事,還是情感態度,都要推崇所謂的“允正執中,不偏不黨”。尤其是信奉“物無美惡,過則為災”的辯證思想。在中國人眼裡,哈內克式的寫實主義似乎顯得過於冷冰冰,缺點人情味。它固然可以揭示生命的真相,卻少了一些面對現實的正向力量。
中國人最講實用理性。與“真相”相比,他們更看重你面對真相的態度和反應,以及延宕其後的社會和文化效益。所以中國人才特別欣賞羅曼·羅蘭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所以中國人的做法,是在無邊的黑暗中,為別人點亮一盞燈火,讓人們暫時免於被黑暗吞噬的恐懼。這是一種典型的東方式的慈悲和軫恤。就像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明明是一個極為陰暗、血腥的故事,卻偏偏要換一種講法,讓它顯得溫暖些、樂觀些。大概這就是東方文化所特有的一種腹語術,它常常會以一種烏托邦式的大團圓結局,去化解現實中那些人力無法克服的生存難題。
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說謝定山和趙歡欣的故事以悲劇收場,代表的是一種“生活的真相”,那麽,常為戒和李慧如作為前者的“鏡像”,其大團圓結局則代表了韓延和大多數觀眾面對“真相”的一種應對態度。有人可能會擔心,這種態度是否過於樂觀,是否會導致對真相的扭曲,或者是否意味著一種對現實的逃避?這種擔心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它恰是浪漫主義者看待世界、看待現實的一種詩意化方式。

有了這種方式,才會有《梁祝》“化蝶”的尾聲;有了這種方式,才會有《巴黎聖母院》卡西莫多和愛絲美娜達的屍骨在墳塋中緊緊相擁的結局。這種方式改變不了現實,卻能讓人們換一種姿態與世界相處。它能用人類自身的想象力超越物質現實的局限,讓人類的精神和情感,飛翔在一個更為遼闊、舒展、自由的詩意化空間。
這也是作為年輕人的韓延,用來觀察中老年世界的一種視線。那是一種來自外部的凝視。這一點,從片名“我愛你”三個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愛你”並不是一種典型的本土情感表達。因為中國人的表達是含蓄的、間接的、托物言志的,很少有“我愛你”式的直白、淺顯和一覽無余。
但年輕的一代似乎更願意接納這種西語式的、乾淨利落、直奔主題的表達方式。所以片名並非是一種為中老年所接受的傳統話語,而是一種屬於年輕世代的時尚話語。它讓影片多了一個敘事層次,那就是關於兩代人生活理念的對話與分歧。劇情中,不論是常為戒還是謝定山,兩人在與子女相處上似乎都遇上了一些麻煩。特別是謝定山和趙歡欣,基本處在被子女嫌棄和排斥的位置。所以才有了常為戒替老友發泄不平,揮鞭怒砸酒宴的場景。

但事實上,在當代中國社會,兩代人之間究竟應該如何相處?也的確是個懸而未決的難題。傳統倫理主張孝道,不太願意拉開長幼之間的距離,但搞不好又會讓兩代人彼此過度介入,乃至干涉對方的生活;現代倫理鼓勵老年人獨立自主,崇尚生活方式的個性化選擇,擺脫對子女的過度依賴。
可是,一旦獨立過頭,又會像常為戒那樣,與子女產生親情的裂隙,儘管兒孫滿堂,也依然會讓自己陷入孤獨無依的生活陷阱。這就如同在雪地裡烤火,距離太遠感受不到火的溫暖,距離太近又會被火灼傷,如何拿捏分寸,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似乎是中國當代家庭倫理所面臨的一道兩難選擇題。
在劇情中,導演並沒有就這個問題展開更近一步的討論。但當我們看完影片,轉頭回到現實生活,我們就會很快發現,老年化社會就像一列飛馳的高鐵,正以某種意想不到的速度向我們迎面駛來。尤其包括我們自身在內,也在一天天地老去。或許將來的某一天,我們也會面臨著與常為戒、謝定山同樣的生活難題。我們必須要好好想一想,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們是否會有一套比劇情更高明、更可行的應對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