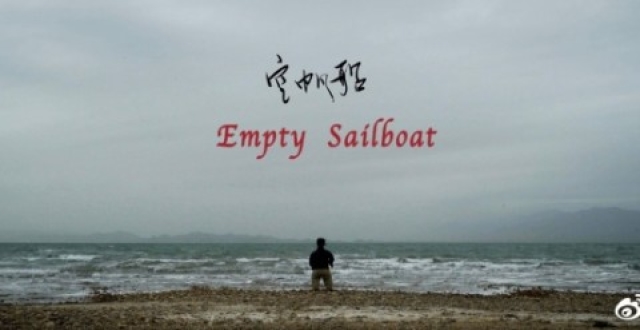近日,電影《大三兒》悄然登陸電影院線。這部小成本紀錄片雖然排片不多,但一上映就收獲不俗口碑,追捧者眾,那一句“我愛這艱難又拚盡了全力的每一天”溫暖著在這座城市裡辛勞打拚的千千萬萬普通人。
佟晟嘉,電影《大三兒》導演。早年間曾任職“善所音樂工坊”吉他手,參與世界音樂專輯《彼岸》部分歌曲的前期錄製。後長期擔任紀錄片導演,紀錄片作品有《幸福中國》《天下華人》《青春致敬青春》《尋找日本》《赤水河》等。

北青藝評:您是如何從音樂走上非虛構影像創作之路的?
佟晟嘉:我這個轉行非常被動。我酷愛音樂,上初中時聽了人生中第一張專輯《夢回唐朝》,從此開始聽各種各樣的音樂,也想從事音樂方面的工作。但是家裡人都不太同意,以至於當我想繼續深造的時候沒有錢來支持,去考試的路費都是大三兒幫忙湊出來的,二十年前的兩千塊錢,是一筆巨款了。之後也參加過一些演出和比賽,做過KTV曲目“扒帶”,也做過編曲,但是一直不太滿意,因為音樂的表達和我心裡的預期差得很遠。直到有一天給一個傳媒公司投了音樂製作人簡歷,這個公司卻讓我去當編導。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個職業,中間又有很多波折,但最終陰差陽錯地當了導演。
可以說本來做非虛構影像的導演只是一個職業、一個差使,但是當逐漸習慣並且喜歡上非虛構影像之後,它就變成了我的一種表達方式。直到後來出現了創作上的瓶頸,對於很多事情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價值觀也不清晰了,又開始真正研究非虛構的創作。
北青藝評:做音樂和做紀錄片有什麽不同?
佟晟嘉:對我來說,舞台上的每一刻都是所有情緒的匯聚和釋放,一個表演者最大的責任可能就是讓觀眾高興起來。雖然我一直刻苦地做音樂,但某種程度上可能是迷失的,這可能也是我一直做不好音樂的原因。
紀錄片則不同,它一方面給了我另一種表達方式,讓我可以在創作的過程中回歸理智,讓大家與我一起思考,擺脫偏執的憤怒、瘋狂、控訴——單純地展示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夠公平的;另一方面,我並沒有在紀錄片中摻雜太多個人因素,把我的夢想賦予它,讓它承擔一個神聖的職能,這就讓創作非虛構作品的目的變得單純起來。當然,我對紀錄片的看法、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也是在不斷完善的。
北青藝評:哪些作品對您的創作產生過重要影響?
佟晟嘉:有一部仍然在傳統媒體播放的紀錄片欄目,就是吉林衛視的《回家》,這檔節目火了很長時間,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限制導演,唯一的要求就是嘉賓的分量要足。應該說這個欄目講述的方式、敘事的結構,對我來說有很大影響。
北青藝評:做“大人物”和大三兒這種“小人物”有什麽區別?
佟晟嘉:開始會覺得有區別,但真正深入地拍攝大三兒之後我才覺悟到,以前所拍攝的那些人物,打動我的地方也並不是他們身上的“標簽”,比如大藝術家、政治家,而是他們的生命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綻放的光芒。他們有的推動了文明的進程,比如裘盛戎、華羅庚等等,這是一種震撼;但也有那種小而美的愛情,同樣讓人感動,甚至小說都編不出這樣的故事來。而像大三兒,他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的生命歷程也是那麽的精彩,當我們認為所有人都無法走過那個艱難時刻的時候,他卻走過來了。這種“正向”的能量不是口號式的宣傳,而是人物在周圍環境足夠黑的時候能從內心激發出的強大能量。大三兒身上有一種“江湖氣”,他很局氣、很仗義,又怕給人添麻煩,這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北青藝評:大三兒去西藏的這個行為,是否跟他所說的自己不需要淨化、與他對您的反問“我不純潔嗎”有所矛盾?
佟晟嘉:我認為並不矛盾。一方面,我們對西藏、對任何事物都是戴著一副有色眼鏡看待的。所有人都會覺得去西藏是一種淨化,構建了一種西藏的意義,但恰巧大三兒並沒有戴著這副眼鏡。他就是想去看看,僅此而已,他與朋友們一起去到西藏,可能比去那裡被“淨化”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大三兒是一個站在命運終點的人。我們對明天有很多規劃,大三兒與我們不同,他對明天的規劃就是準備好迎接驚喜,這讓他超脫於我們之上。在片中,他到了大昭寺也不願意跟神明妥協,珠峰是沒法淨化他的。有觀眾也問我《大三兒》這部紀錄片會對他造成什麽改變,實際情況是:不會對他有什麽改變。
北青藝評:您在片中也出鏡了,如何看待自己在影片當中的角色?
佟晟嘉:在燒烤店一場戲拍出來之後,我就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回避。既然不能與之為敵,還不如與之為伍。我認為我在這部片子裡的功能非常簡單,就是司機。從紀錄片的手法上來說,我的經驗就是把自己做好,我並不在乎別人如何做,或者紀錄片“應該”怎麽做,我不認為有這樣的定法。以往十年的經歷都在告訴我這一點。
北青藝評:片中的工廠為什麽會有那麽多殘疾人?
佟晟嘉:《大三兒》裡的這家工廠是一個國企。國企也有義務和責任為當地人,尤其是這樣的邊緣群體解決一些就業問題,所以類似的國企會為他們安排一定數量的崗位,國家也會以各種方式鼓勵企業這麽做。當然,這些殘疾人的工資也不會很高,會根據不同工種有所浮動。大三兒在這個地方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生活不能算是很困難,公司給他五險一金,工資也足夠生活,節假日會有三薪,他的父親有退休工資,兩個人也有房。但如果是旅遊的話,就會拮據一些,需要借錢來走完這一趟旅程。
北青藝評:赤峰這座城市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麽?
佟晟嘉:我原來很不喜歡,覺得它限制了我很多。但這一次也是借著拍《大三兒》的契機,借著大三兒對我提出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如果世界上紀錄片導演這個職業消失了,你該怎麽辦”,重新理解了我的處境和我自己的故鄉。
我發現自己跟朋友們的交流太少了,而我生命中的能量,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那一片土地。那裡的人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有自己獨特的幽默,而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分子。片中出現了很長一段掃墓的片段,有觀眾對我說這一段大三兒說的話“太好了”,但事實上這是赤峰人每年清明一定會做的事情,我們會覺得那一個個躺在地上的墓碑是鮮活的。
北青藝評:片中很多次出現了水龍頭滴答水的鏡頭,這有什麽特殊含義?
佟晟嘉:水龍頭總是關不嚴,這是我腦海中一個十分強烈的記憶,它讓我想起我的祖輩,讓我本能地感到親切。它好像就象徵著一種生活常態,也很像大三兒本人的狀態,像“人生的前列腺”,總是出問題。另外,水龍頭漏水本身也在這個城市的節奏之中。這個鏡頭能給我很多這樣那樣的聯想。

北青藝評:您對這個片子是否有一個設想?據我們了解,大三兒去西藏這件事情完全是一個偶然事件,發生在您決定拍他之後。
佟晟嘉:是這樣的。但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去掉原先的設想,隻用那些沒有受到人為影響的“邊角料”。我受到的訓練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沒有剪不出來的片子。舉例來說,如果大三兒這一趟並沒有成行,整個片子裡他就是在不停地查資料、體檢、打電話,為了生活、為了去珠峰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結尾還是他灰溜溜地去買彩票,說一句“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這種張力會更強,片子沒準會更好看。但實際結果是,他去了西藏,而且自己站在了珠峰腳下。這表明,非虛構影像從任何一分鐘開始、在任何一分鐘結束,都不會難為情。我們設計的情景,遠沒有生活給我們的有趣。我從不擔心自己拍不到東西,只要願意陪著主人公出入各種平常可能會嗤之以鼻的環境,願意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最終都可以得到生活的精彩。
北青藝評:影片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和問題?
佟晟嘉:我在拍攝現場的狀態會比較強勢,一般很少解釋為什麽這樣拍。這就是紀錄片拍攝的特點,一切都是轉瞬即逝,而我們的整個攝製團隊也經過常年合作,所以哪怕我們的單條素材都能夠達到二三十分鐘,攝影師也可以用攝影機進行蒙太奇,不會出現太大問題。
北青藝評:您如何看待紀錄片真實性的問題?如何對自己拍攝的素材進行選擇?
佟晟嘉:我認為真實和謊言,前者是“事實的部分”,後者是“部分的事實”。在紀錄片拍攝的過程中,我會面臨很多選擇,選擇的標準就是“良心”,是我從業十幾年以來所形成的一種價值,我要讓我的作品對得起這個世界。
具體到這部作品來說,大三兒經歷了這樣那樣的命運,而我的每一個抉擇都要圍繞他生活中最需要的東西來展開,這個東西就是“情”字。親情、友情,還有陌生人之間的“共情”(尤其是西藏人為大三兒獻哈達的段落),是讓他最終得以抵達珠峰大本營的關鍵和核心。每個人心中都有這個“情”字,但在這樣一個資訊時代,我們可能會忽略掉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關係。《大三兒》應該是一面鏡子,讓人們看到這個時代命題。

北青藝評:目前有沒有新的拍攝計劃?
佟晟嘉:目前的計劃是拍攝一個非虛構影像三部曲,《大三兒》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叫“城市猴子”,講的是一群“跑酷”的80後,從一群二十歲出頭的毛頭小子,到現在有了自己的運動場館,肉眼可見臉的變化出現在十年間的素材裡。有的人已經有了家庭,有的人還在不斷換女朋友,有的人已經離開了這個團隊……這部片子講述的就是他們的生活狀態,目前已經有了五六百小時的素材,預計今年可以殺青。
另外一部是女性題材,叫“這個女人”,講女性站在傳統道德的邊緣,對幸福的要求、看法和對幸福的詮釋。這一部的創作周期會更長一些。出於對主人公的保護,這一部可能會成為一部私人的“禮物”,不會走上院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