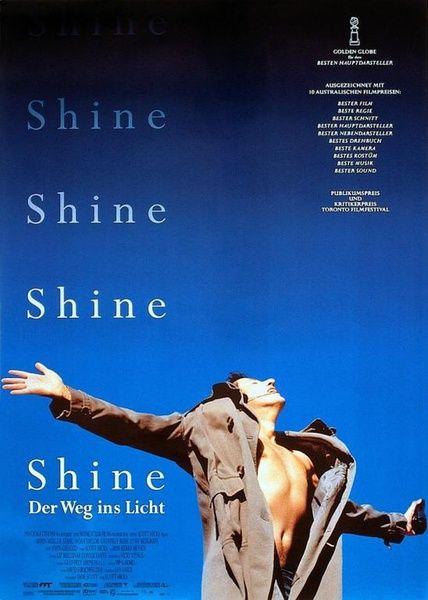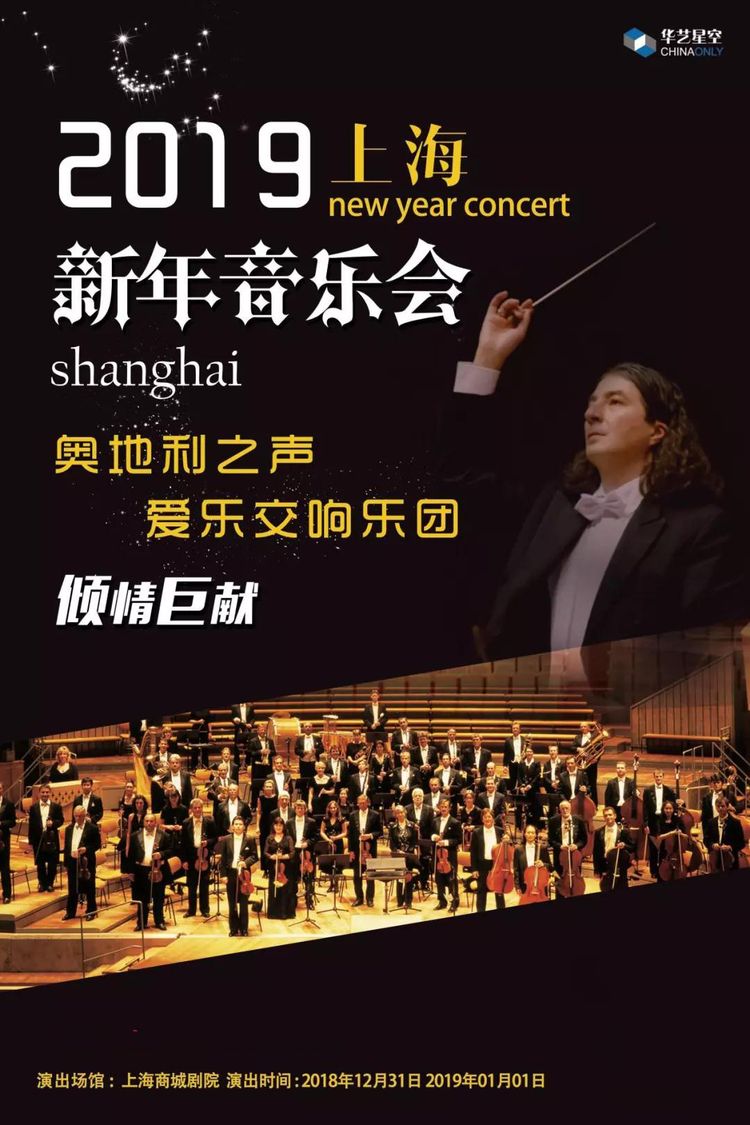莫敏妮
“我平生最大的心願,就是在玫瑰花盛開的季節死去。”雨果曾這樣說,他陶醉於美,活了83歲。浪漫主義者對待死亡,自帶唯美因子,生命就如文學分析,以美為起點,以美為終點。法國詩人拉馬丁認為“生同春光,死如玫瑰。” 生命,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終有一別。人類寬廣的心靈並非真的軟弱到不堪一擊,以至不能抵禦和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培根指出:死亡無法征服那種偉大的靈魂。這種人,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也始終如一,不失其本色。今夜,聽聽偉大作曲家所作的人類哀歌,我們不僅聆聽,而且可以像哲學家一樣思考人類古老恆常的話題,經歷一種西方觀念:人不必懼怕進入黑暗再重見光明的過程。

愛情的力量,會讓人不懼怕死亡。奧古斯都大帝在彌留之際,他唯一關注的只是愛情:“永別了,麗維亞,不要忘記我們的過去!”在熾熱如火的激情中受傷的人,是感覺不到痛楚的。我們聽聽徘徊於生死邊界之時那些動人的哀歌。

“愛之死”
美與死亡這種典型的浪漫主義結合,經由瓦格納的悲觀渲染而特見加強。在瓦格納的音樂裡,尤其是《特裡斯坦和伊索爾德》中,令人心旌搖蕩的情色與悲劇命運組成雙重主題,而以複調音樂賦予一元結構。美的命運不是在激情中獲得實現,而是在為愛而死中完成:美從世界的天光退出,透過唯一可能的結合形式,即死亡,滑入暗夜力量的懷抱。瓦格納抒寫中世紀愛情悲劇,他讓特裡斯坦仿佛在夢中甦醒,來到夜幕下的神奇天堂,他借伊索爾德面對死亡而唱出了一曲熱愛生命的歌謠。此時想起李斯特彌留之際喚出的那句:特裡斯坦和他追逐一生,卻終留遺憾的愛情。李斯特留下柔情夢幻的《愛之夢》,瓦格納譜寫了微笑赴愛情之約的《愛之死》。用音樂表達情感果然是最真摯感人的,也惟有音樂才能抒寫生命的極致。

“當我長眠地下”
狄朵在臨死前悲慟唱出的“當我躺在黃泉之上”,是最著名的“哀歌”之一。看“英雄女高音之母”弗拉格斯塔(Kirsten Flagstad)的紀錄片,一開頭就被一首優美哀愁的女高音唱段所吸引,我幾乎一下子就辨聽出,這是這位瓦格納女高音所唱的“當我長眠地下”。羅馬人的故事是屬於全歐洲的,從特洛伊毀滅火海中逃出生天的埃涅阿斯王子,經過北非迦太基,一不小心就與狄朵女王傾心相愛了。但神旨意埃涅阿斯須渡海北上到意大利重建邦國,於是埃涅阿斯不得不離去。狄朵女王在貝琳達陪同下前來送行,在埃涅阿斯的船駛離後唱起這首高貴傷感的哀歌,她最終在萬箭穿心的極度痛苦中自戕。最後反覆吟唱著一句:“毋忘我!但是啊! 忘記我的命運。”沉浸在這首哀歌中,真有不能言說的痛楚。亨利·珀塞爾是屬於全歐洲的英國作曲家。“雖然珀塞爾的音樂中能聽到歐洲各國的音樂特質,但珀塞爾仍然是一位地道的英國作曲家。”巴洛克美聲,擁有無比寬廣的深情,散發著一種古老而特別的光澤。

“葬禮進行曲”
巴洛克之美神鬼冒險,其藝術常借醜宣揚美,以偽表真,通過死亡呈現生命。“死亡”尤為巴洛克心理念念常在的主題。當然,這個主題也可見於莎士比亞等非巴洛克作家。西方古典音樂尤其體現對生命的尊重,人從出生到結婚,直至死亡,都有高貴的音樂來表達一種儀式感。涉及葬儀,悼歌不斷,安魂撫慰。巴赫《降B小調前奏曲與賦格》(《平均律》第一卷第22首(WTC I/22,BWV867)可謂開“葬禮進行曲”先河之作。亨德爾在清唱劇《掃羅》中也有類似的“死亡進行曲”,呈現呂利進行曲的遺風,同音反覆,旋律凝重。而珀塞爾為瑪莉皇后所寫的《葬禮進行曲》則顯得簡單樸素,鼓號皆沉。什麽樣風格的曲子算是“葬禮進行曲”?緩慢、同音反覆、沉重持續的行進步伐、連續附點、小二度音程主導等成了哀樂的主要特徵。

貝多芬
《降A大調奏鳴曲》(Op.26)第三樂章
《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Op.55 英雄)第二樂章
英雄之死,猶如峨峨若千丈松崩。貝多芬一直堅持啟蒙運動、古典主義的理想,堅持貴族卓越品質的顯赫價值,即使這些由於歷史的發展,變得跟不上時代之後,他亦如此。他對英雄的崇敬與他的英雄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他的《降A大調鋼琴奏鳴曲》(Op.26)第三樂章與《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Op.55 英雄)第二樂章,都是為英雄而寫的“葬禮進行曲”。他的“葬禮進行曲”體現一種崇高精神。崇高是偉大靈魂的回響,也是藝術的效果。崇高乃宏偉、高貴的熱情,如荷馬史詩或偉大古典悲劇所見的表現,使藝術品的創作者與體會者情動神馳。

《E小調葬禮進行曲》
清新流麗的門德爾松《E小調葬禮進行曲》選自《無詞歌》(Op.62 )第五集第三首。維特根斯坦曾說過:“我猜想門德爾松”是作曲家中最無悲劇色彩的。” 的確,富足幸福的門德爾松像是從來不知人間憂愁的精靈,他無憂無慮地坐在無花果樹下寫。他的音樂不見悲天憐人,也不見沉憂肅穆,卻總是甜美如歌,聆聽起來沒有任何難懂之處。就算沉重的“葬禮進行曲”,他擲筆即成一首如印象派色澤閃爍的鋼琴小品。可以說只有駭人的標題,而沒有實質的可怖,倒是美得不像世俗的哀樂,和聲綽影若隱之間,盡是連綿不絕的回憶。

“葬禮進行曲”
肖邦《葬禮進行曲》中間一段簡直是“雲飛水動,意出塵外”之夢幻,可以說像他的夜曲,旋律的裝飾性變化具有較強的即興色彩。雖然比不過印象派朦朧變幻的多情和聲,也比不過貝多芬那些狂叩內心的思辨,卻用這首作品打敗了肖邦自己,感動無數人,雁過長鳴,絕世留聲。勝利者聽起來美好如臨風浩歌,失敗者聽起來淒美如愁人兮奈何!如果是不勝不敗的內心,則進入一種共情之境,融入肖邦的琴詠之中寄托故國相思。

“齊格弗裡德葬禮進行曲”
瓦格納的樂劇具有宏大的管弦樂音效,真的令人熱血沸騰。他的“齊格弗裡德葬禮進行曲”在《尼伯龍根的指環》第四部《諸神的黃昏》中出現,恰好地表達出作品中“宏偉”及略帶一絲“幽深”,充滿另類的哲思。瓦格納不愧對聲音有著偉大的理解力,或者說是直覺。不斷重複著沉重的警示性短樂句,象徵齊格弗裡德的悲劇,展示了這位無畏的、對權力和財產感到陌生的英雄,在這個“陰險狡詐的世界”中,是注定要失敗的。瓦格納心中關於英雄的葬禮不同凡響:英雄時運不濟,也只能低下不甘的頭顱。在我們印象中,瓦格納音樂中英雄人物的葬禮是這樣的:射箭點燃運載英雄靈柩的鳳船上乾草易燃物,一切在遠去的熊熊烈火中,都被吞噬而結束,人間英雄回歸天神的列席。如同冬去春來萬物復甦的自然循環,一切又將重生。在所有葬禮進行曲裡面,還是被這首震撼,沒有悲哀,聽起來卻是蕩氣回腸。

《諾爾德拉克的葬禮進行曲》
這是格裡格懷念故友的哀樂,是一首真正意義上的“葬禮進行曲”。宏偉遼遠的小號音效,帶著聆聽者進入一個莊嚴肅穆的葬儀氣氛。“突然間我周圍的世界一片黑暗!諾爾德拉克死了!噢!我最好的朋友!”1866年4月初,格裡格用陰鬱的A小調慢板,寫下了他一生中最悲情的旋律《諾爾德拉克的葬禮進行曲》,為悼念他的摯友諾爾德拉克的去世。正所謂故人朋舊,漸就凋落,深可慨歎。悲從中來,不可斷絕。

柔板,纖細而富於情感,最容易透露作曲家的內心,憂傷也最容易藏於其中。我在柔板聽見歎息聲,也看到隱藏的眼淚。聽:我的和弦開始慢板的滄桑。
布魯克納
《第七交響曲》柔板
布魯克納《第七交響曲》的柔板樂章是致瓦格納的悼歌,與貝多芬《英雄》的第二樂章、瓦格納的齊格弗裡德之死並稱為三大葬禮進行曲。長達23分鐘的柔板,哀而不傷,將弦樂的顫音發揮到極致,更兼有感恩讚的崇高,不論是自身的感染力還是後來招致的議論都讓這個樂章成為音樂史上最有名的柔板之一。布魯克納特立獨行,是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他在瓦格納去世前一個月,已預感到自己的偶像死亡在即。布魯克納創作這部交響曲時,即傳來瓦格納去世的消息,而他還在其中運用了瓦格納大號的名樂段,所以這一樂章被認為是向瓦格納致敬的挽歌。後來,當布魯克納去世時,維也納愛樂的銅管組自發組織起來在布魯克納的葬禮上演奏此樂章的旋律。再後來,這首交響曲成了卡拉揚最後指揮的“天鵝之歌”,三個月後他心髒病突發離世。卡拉揚的演繹甚至超越了布魯克納的音樂想象,執棒傾情而獨出機杼,長揖塵凡而不流於悱惻。難道大師都有不同凡響的直覺?


弦樂柔板
烏雲掩映,寒鴉哀鳴,黃昏至暗黑的悲歌,有時候聆聽還需要勇氣。美國現代作曲家山繆·巴伯的《弦樂柔板》,我一直不敢聽。為什麽?說來有個小秘密,一次去參加葬儀,回來後至今不肯插白色的百合,那味道,總覺得有不安的聯想。英國廣播公司曾做過一個聽眾調查,選出世上最悲傷的音樂——結果不出意料,山繆·巴伯的《弦樂柔板》得票最高。由於寫這篇文章,我內心一度掙扎,聆聽吧,我怕這哀樂引起憂愁,據說整曲自始至終沉浸在難以排遣的悲哀之中,人們常常把它與絕望與死亡相聯繫。昨晚,我鼓起勇氣按下開始鍵。音樂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樣令人顫抖,不過就是用些緩慢、重複、冗長的句子營造一種揮之不去的哀感。

《為逝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曲》
拉威爾這個堅強的一戰幸存者,說他曾有過唯一的愛慕對象就是音樂。他的音樂有著一種低調而溫暖的魔力,他的舞曲不僅有悠然起舞的《波萊羅舞曲》,還有精致唯美的《為逝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曲》。飄著淡淡憂傷的《孔雀舞曲》是沙龍中最受歡迎的曲目之一。如此短小曲子卻有三個譯名:死公主的孔雀舞、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和為逝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曲。哪一個更符合音樂基調,或又能更加渲染故事本身的悲劇色彩?“死公主的孔雀舞”雖不夠規範,但這樣的標題似乎更能一下子抓住人心,讓人瞥見那一抹幽深的孔雀綠,讓人發起一種“綠袖子”的幽思。當作曲兼指揮家瑪挪亞·雷德特德斯科(Manoah Leide-Tedesco)問到怎樣理解曲名“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拉威爾輕輕一笑,答道:“你以為?標題和內容沒有一點關係,我只是喜歡這幾個詞,恰好放在這。就是這樣。”《為逝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曲》創作於1889年,當年拉威爾還是巴黎音樂學院的學生。據說他的靈感來自羅浮宮裡面一幅公主肖像畫;另一說則是源於西班牙教會的葬禮習俗(在下葬死者前,在祭壇靈柩前,莊重地跳一次孔雀舞)。於是,人們仿佛置身於博物館的公主畫像前,緩緩吟誦:如果我能偷偷將此刻定格為瞬間,畫一張完美的笑靨,那樣,我們的故事便會永遠豔鮮,我們永遠不會說再見。

在我們的淚谷裡,有一種不知其名的永恆的呻吟,成了人類哀歌的根本或主調。“覺來落月明窗戶,撫枕潸然淚滿床”,讀來悽愴不已,誰會記得七百年前一個六十五歲老人的深夜咽哽!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然而,人之所以為人,不在於比他物擁有更加完美的世界,而在於生命有足夠的寬度,來容納那些支離破碎;有足夠的能量,來抵銷那些顛沛失意。苦難與死亡,這些就如同春江與落花一同漂去無人知道的遠方。換一個思維去看,歲月極美,也在於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