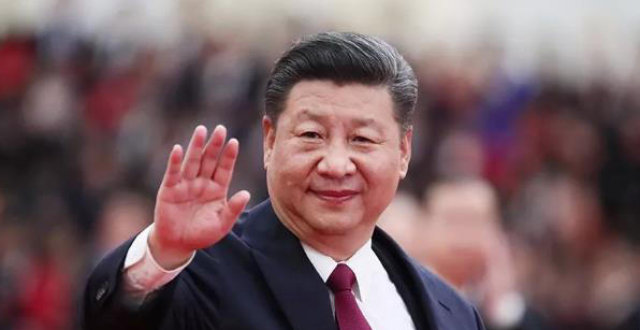一切事物的單調包圍著我,就像我進了監獄。
而今天是我獄中歲月中的一天。不過,那種單調只是我自己的單調。其實,每一張即便是昨天與我們相逢的人面,在今天也有了完全不同之處,因為今天不是昨天。每一天都是特定的一天,世界上永遠不會有另外的一天與之相似。只有在心靈中,才會有絕對的同一(儘管是一種虛假的同一),使很多事物與很多事物相類聚並且被簡化。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組成的,我們的弱視症使我們只能看到四處彌漫的薄薄迷霧。

我希望能夠遠走,逃離我的所知,逃離我的所有,逃離我的所愛。我要出發,不是去縹緲幻境中的西印度,不是去遠離其他南大陸的巨大海島,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不論是村莊或者荒原,只要不是在這裡就行。我嚮往的只是不再見到這些人面,不再過這種沒完沒了的日子。我想做到的,是卸下我已成習慣的偽裝,成為另一個我,以此得到喘息。我想要睡意臨近之感,這種睡眠是生活的期許而不是生活的休息。靠著海邊的一個木棚,甚至崎嶇山脈邊緣的一個山洞,對於我來說都夠了。不幸的是,我在這些事情上從來都是事與願違。

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
不會有其他的法律,因為這條法律必須被人們遵從,沒有造反或另求庇護的可能。有一些人生來就是奴隸,有一些人後來成為奴隸,還有一些人則是在強製之下被迫為奴。我們所有人對自由怯懦的愛,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我們的奴隸生活是如何與我們般配——因為一旦自由降臨我們,我們全會將其當作一件太新鮮、太奇怪的東西而避之不及。甚至,我剛剛表達了我對一個木棚或山洞的願望,希望在那裡解除一切事物的單調,也就是說解除我之為我的單調,我真正有膽量動身去那個木棚或山洞麽?單調一直存在於我的內心,我知道並理解這一點,我是否因此就再也不能從中解脫?到哪裡都是窒息,因為無論我在哪裡都是我在那裡,當整個事情與空氣無關而是肺出了毛病的時候,我的呼吸還能在什麽地方得到改善?誰能說我情不自禁地呼喚純淨太陽和空曠田野以後,呼喚明亮海洋和廣闊地平線以後,便不再會惦記我的床或我的食品?不再會走下八段樓梯來到街上?不會再次拐進街角的煙草店?不會再次對身邊閑得無事的理發匠問候早安?

我們周圍的一切,成為了我們的一部分,成為滲透我們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經驗,就像巨大蜘蛛之神布下的網,在我們輕搖於風中的地方,輕輕地縛住我們,用柔弱的陷阱誘捕我們,以便我們慢慢地死去。一切就是我們,而我們就是一切。但如果一切都是虛無,那麽事情還有什麽意義?一道陽光暗去,一抹突然陰沉逼人的烏雲移來,一陣微風輕輕吹起,寂靜降臨了,抹去了這些特定的面容、這些嗡嗡人語,還有談話時的輕鬆微笑,然後星群在夜空中如同殘缺難解的象形符號,毫無意義地浮現。

作者簡介——
費爾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詩人、作家,葡萄牙後期象徵主義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使命》、《惶然錄》等。
1888年生於葡萄牙裡斯本,父親在他不滿六歲時病逝,母親再嫁葡萄牙駐南非德班領事,佩索阿隨母親來到南非,在那兒讀小學中學和商業學校。在開普敦大學就讀時,他的英語散文獲得了維多利亞女王獎。1905年他回到裡斯本,次年考取裡斯本大學文學院,攻讀哲學、拉丁語和外交課程,後退學。他常去國立圖書館閱讀古希臘和德國哲學家的著作,並且繼續用英文閱讀和寫作,死於1935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