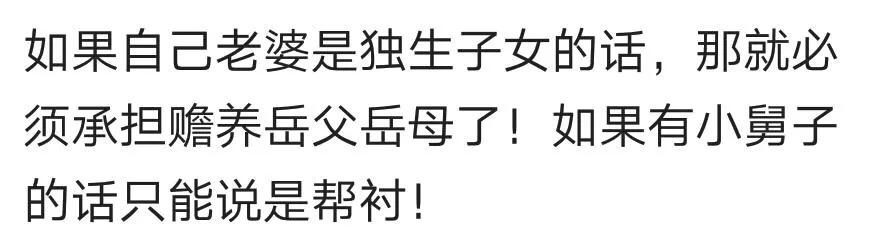“義父”也稱契爺、契爸、乾爸、乾爹、假父。結乾親認義父這等事情真可謂是“古已有之”,更確切地講是古今中外皆有之的事。原因則各不相同。在我國南方一些地區,結乾親的主要原因是封建迷信行為,有認為認義子女可以化解夫妻雙方命理中存在的婚外情傾向的;也有父母因為所謂“雙爹雙娘,福大命大,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給子女認乾親彌補命理不足的;在一些地區則有將民間信仰中的神明,例如媽祖、土地公、關公、保生大帝、清水祖師等熱作乾爹乾娘的。
在日本櫪木縣的川俁地區,當地年滿二十歲的男性青年會參加一月舉行的“元服式”,類似成人禮,儀式的內容就是與非同族年長男性結成擬製的親子關係。這種習俗是為了鞏固當地的社會關係。在過去,生產力水準有限,多子家庭能夠繼承的財產有限,為了防止家族內部兄弟鬩牆,家中次子以降的兒子都會參與“元服式”,擴大家庭關係,維系社會穩定。
當然也有許多因情誼行為結下的乾親,這點在明清小說和近現代武俠小說中十分常見。明末話本小說《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一》中有“舍人把認了義父,認了應襲指揮,今義父現在京營做遊擊的話,說了一遍。”
清代儲仁遜小說《劉公案-青龍傳》第一回“訪惡霸途認義女,疑拐帶路打不平”中就有家中蒙願的湯美容當街認親的描寫。“湯小姐聞說是非親非故,不管奴事,心中暗想:‘此位先生人品端正,非是歹人,不如認了乾親罷。’湯美容乃系紅鸞星降生,受些折磨方可見天日,當享榮華。一時機靈,小姐口呼:‘義父,女兒這裡叩頭了。’”萍水相逢的“皇爺”動了惻隱之心,收她做義女,才有了後續的故事。
清代李汝珍《鏡花緣》中也有駱龍讓自己孫女駱紅葉拜認乾親的段落,“駱紅葉一面哭著,走到唐敖面前,四雙八拜,認了衣服。又與多、林二人行禮。因向唐敖泣道:‘侄女蒙義父天高地厚之情,自應隨歸故土。’”可見自願結乾親的情況下,既可以是尊親屬做主、也可以自己做主。
自願接下的乾親總歸有一種人情和情義在,重情重義者不能背叛這種關係。金庸《倚天屠龍記》第十回“百歲壽宴摧肝腸”裡有“她(殷素素)身子微微一顫,說道:‘孩子,你爹爹既然死了,咱們只得把你義父的下落,說給人家聽了。’(張)無忌急道:‘不,不能!他們要去害死義父的,讓他們打死我好了,爹爹不說,我也決計不說。’”簡單幾句話就塑造出了張翠山、張無忌父子俠義形象,張無忌與義父謝遜的關係更是全書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義父子關係很難被讀者忽略。

相比近現代文學創作,古代史料記載中的義父子關係則複雜得多,留下的道德灰色地帶也更加寬廣。上古以降至唐代,義子、假子與異姓養子在書面記錄中很難通過名稱得以區分。洪邁《容齋隨筆》“人物以義為名”條中有“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 翟灝《通俗編》“義父”條則雲:“項羽尊懷王為義帝,猶假帝也。唐人謂假髻曰義髻,彈箏假甲曰義甲,皆以外置而合宜者。故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子、義女。”這裡的假子、義子都是指自外姓人家收養的非親生子女。隋唐五代之軍將、宦官多養假子以壯聲勢,如《舊唐書》說“(杜)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唯闞棱、王雄誕知名。” 而同傳其前稱闞棱為其養子。《新唐書》說張亮養假子五百,而《舊唐書》謂其畜養“義兒五百”。唐代宦官喜好養子,《舊唐書》先稱“內官高延福收(高力士)為假子”,稍後則曰“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五代時郭氏夫婦所養義子不肖,與嫡子訟,張希崇判詞:“雖雲假子,辜二十年養育之恩。”可見義子與義兒、假子可以互通,都是養子的異名或別稱;相對地,義父、假父也可交替使用,其實也就是養父。隻不過在收養名目之下,有的為家族侍養與繼嗣,有的則為擴充自己勢力。
異姓養子與義子、假子詞義混淆,但假子、義子不一定表明一定存在收養關係。《史記.呂不韋傳》集解引《說苑》嫪毐醉言:“吾乃皇帝假父也。”翟灝《通俗編》曰:“若史遷呂不韋傳所雲,假父乃與後世義父不同。”這裡的假父,應該不是指養父,可能較接近於繼父。漢初《二年律令》有所謂“叚(假)大母”,顏師古注《漢書.衡山王賜傳》“假母”為:“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史記.衡山王傳》集解引《漢書音義》則釋為“傅母屬”,即傅母、養母、乳母之類。在古代尚未明確分化,各種不同的身分關係混淆在一起,而泛稱為“假”,其實都是指非親生的、沒有血緣關係的。
“假”一定不是真的,“義”不一定是真的。令現代人印象最深刻的典型事例是元末明初羅貫中章回體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第三回“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饋金珠李肅說呂布”中到處認爹的呂布:“公若不棄,布請拜為義父。”呂布人品雖然被作者詬病,言必稱“三姓家奴”,但畢竟不是所有的“義子”都像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有揭竿起義、反抗義父的能耐,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許多“義子”不過是變相的奴隸而已。
明清時期的福建海商有認義子的習俗,周凱《廈門志·風俗略·俗尚》記載,海商買貧家男孩為契子,養大派去出海,我國社會經濟史奠基人傅衣凌先生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一書中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奴隸制度。汪文芳《增補書柬活套》收錄一份投身為義男(契子)的文書,這份投靠文書載:“立靠身文契:(投身者名字)行年(歲數)系(府名)府(縣名)縣人,因家貧無食,央中(投身者名字),情願投靠到某府為義男……”投靠者與被投靠者只是名義上的義父子關係,實際上是一種終身製的廉價勞動力,這種制度是因當地從事海上貿易者不願自己的親生兒子出海冒險,於是收買貧困家庭的男性為“契子”,由於關係被排除官方管轄範圍,因而成為了道德上的灰色地帶,在福建兩廣等海運發達地區,“契子”也常常被視為同性性行為的承受方。
拜認乾親結義父子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特定的社會情境中或許承擔著擴張社會關係的良性所用,但是這種類比親屬親密關係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存在著廣闊的曖昧太空,在存任何權力關係中,不對等的權力雙方結成的類似關係對相對弱勢的一方都是弊大於利的,同時也為涉道德問題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乾親關係的曖昧之處在於它往往成為回避其他更嚴重、更深刻問題的擋箭牌,將真相掩埋,阻礙正義大踏步到來。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